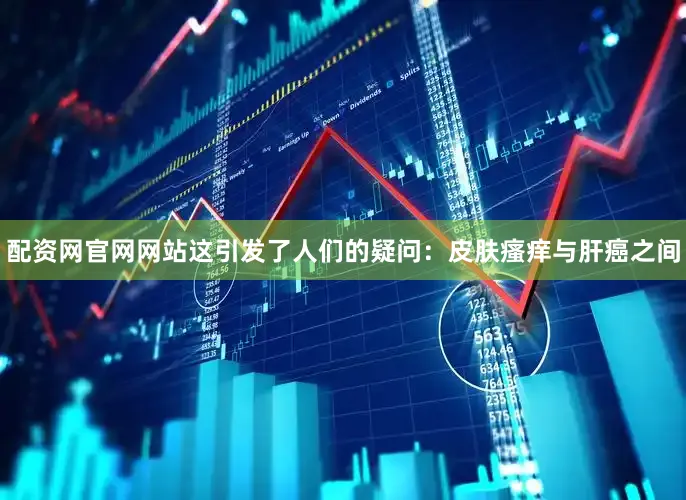一场由总经理越权签约引发的千万赔偿纠纷,揭开新《公司法》下公司治理的权力重构。
2024年底,A科技公司会议室里弥漫着紧张气氛。持股仅8%的总经理乙在未获董事会授权的情况下,以公司名义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1500万元的技术服务合同。这份合同不仅超出公司章程规定的经理决策权限,更与公司战略方向严重背离。
当B公司要求履行合同时,A公司董事会震惊地发现:新《公司法》实施后,他们尚未修改公司章程中关于经理职权的条款,也未通过正式授权明确乙的权限边界。
这场纠纷背后,是新《公司法》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——经理职权从法定列举变为章定授权,这一变化正在悄然重塑企业股权架构的权力平衡。
01 案件背景:一场由职权模糊引发的公司治理危机
A科技公司是一家典型的股权分散型企业。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8%、15%和12%,其余55%股权分散在二十余名小股东手中。2023年股东会任命乙担任公司总经理,授权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。
2024年7月新《公司法》实施后,A公司未及时修订章程。乙作为总经理,依据原《公司法》规定的“法定职权”认知,认为其仍有权签署千万元级合同。
同年10月,乙以公司名义与B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,约定A公司支付1500万元购买一套智能管理系统。签约时乙未出示任何授权文件,仅使用公司公章。
三周后,A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现该合同存在严重问题:该系统与公司现有业务完全不兼容,且价格远超市场均价。董事会立即叫停合同履行,B公司遂提起诉讼要求赔偿。
02 争议焦点:经理职权边界与公司责任认定
庭审中,双方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激烈辩论:
乙是否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千万级合同?B公司主张:根据商事外观主义,乙作为登记备案的总经理,当然具有代表公司签约的职权。且新《公司法》删除经理职权列举后,法律并未禁止经理签署此类合同。
A公司抗辩:公司章程明确规定“单笔超过300万元的交易需董事会决议”,乙签约前未获董事会授权。新法下经理职权应回归“章定授权”本质,不能当然推定其具有全权代表权。
B公司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?A公司出示证据显示:合同签订前,B公司业务员曾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A公司章程中关于重大交易决策权限的规定,但未要求乙出示授权文件。
B公司则辩称:新法实施后,各公司经理权限差异巨大,交易相对人客观上无法核实每家公司的内部授权状况。
03 裁判结果:越权签约的责任划分
某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认定:
合同对A公司不发生效力法院认为,新《公司法》第74条将经理职权明确限定在“公司章程规定或董事会授权”范围内。A公司章程明确限定经理签约权限为300万元以下,1500万元合同明显超越职权范围。
B公司不构成善意相对人证据显示B公司在签约前已知晓A公司章程对经理权限的限制,却未要求乙出示董事会授权文件,不符合交易审慎注意义务,不构成善意相对人。
责任承担方式乙超越职权签订合同,给B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乙个人承担80%赔偿责任;B公司自身未尽审查义务,自行承担20%责任;A公司不承担合同责任。
04 法律分析:经理职权变革的三重冲击波
职权来源的根本性变革
新《公司法》第74条删除了原法列举的8项经理职权,代之以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”的概括性规定。这一变革带来三大影响:
公司自治空间扩大。各企业可根据行业特性、规模大小设计差异化职权方案。科技公司可授予CTO型经理技术决策权,贸易公司则可强化CFO型经理的融资权限。
董事会控制权强化。董事会通过授权文件可动态调整经理权限,在危机时期快速收权,在扩张阶段灵活放权。
章程重要性凸显。新法下公司章程成为界定经理职权的“宪法性文件”,未及时修订章程的企业将面临巨大法律风险。
股权架构的权力重构
股权高度集中时(如控股股东持股超50%),经理往往由控股股东委派。新法下控股股东可通过章程直接规定经理职权,实质强化控制权。但需警惕因此导致的中小股东权益受损风险。
股权高度分散时(如前五大股东合计持股<30%),经理层可能通过章程设计获取超额权力。本案A公司正是此类典型,乙作为职业经理人试图利用职权模糊地带扩张权力。
存在相对控股股东时(如第一大股东持股30%左右),新法下最易形成健康制衡。多个大股东可通过章程精细设计经理权限,既避免“经理独裁”,又防范“股东掣肘”。
交易安全的制度保障
表见代表规则的适用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70条,经理以公司名义实施的职权范围内行为,即使超越内部授权,对善意相对人仍发生效力。但本案因B公司非善意而不适用。
善意认定的新标准。新法下,交易相对人对经理权限负有“基础审查义务”,至少应核查企业公示章程。涉及重大交易时,合理谨慎的商人应要求查看授权文件。
越权追责机制。新法第11条明确:“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,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”。该原则同样适用于经理等职务代理人。
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提示:新《公司法》下,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的规定如同“权力地图”,缺失这张地图的企业,注定在治理迷宫中迷失方向。
05 实务应对:构建三位一体的风控体系
公司章程的重构策略
章定职权模式。股东会直接在章程中详细规定经理职权范围,常见于股东对经理不放心的初创企业。优势是稳定性强,但修改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(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)。
董事会授权模式。章程仅作原则性规定,具体权限由董事会通过决议授予。上市公司普遍采用此模式,便于根据经营需要灵活调整。但需配套完善的授权文件备案制度。
混合控制模式。章程规定核心权限(如重大资产处置权),董事会授予日常经营权。目前多数企业的优选方案,既能防范关键风险,又保持经营弹性。
股权架构的适配调整
优化股东协议条款。投资人应在新版股东协议中增设:“公司修订章程中经理职权条款需优先股股东同意”、“经理任命需符合特定资质条件”等保护性条款。
设置类别股制度。股份公司可通过发行特别表决权股,使创始人在股权稀释后仍能控制经理人选及职权设计,确保公司治理稳定性(新《公司法》第144-146条)。
建立表决权拘束协议。多个中小股东可签订一致行动协议,联合提名董事参与经理职权授权决策,防止大股东单方操控经理层。
交易审查的标准流程
建立权限核查清单。法务部门应制作《经理权限确认指引》,业务人员在与经理签约前必须核查:交易金额是否超限、事项类型是否需特别授权、相对人是否关联方等。
创设授权公示系统。在公司官网设置“授权查询”专栏,实时更新经理最新授权文件。既履行告知义务,又避免交易相对人以“不知情”抗辩。
采用电子签章系统。通过OA系统设置“电子用印审批流”,自动拦截超越经理权限的用印申请。技术手段弥补制度漏洞。
新《公司法》对经理职权的重构犹如投入公司治理湖面的巨石,其激起的涟漪正层层荡向股权架构的每个角落。当经理从“法定职权”走向“章定授权”,企业面临的是治理模式的全面升级。
那些及时修订章程、完善授权机制的企业,将在新一轮公司治理变革中赢得先机;而那些固守旧规者,可能成为下一个法庭故事的主角。
具体案件需要咨询专业律师。
作者介绍:俞强律师
执业机构: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(高级合伙人)地址: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广场一座12楼教育背景:北京大学法律硕士,具有证券、基金、期货从业资格联系方式:通过君澜律所官网联系专业荣誉:2020年上海律师协会“金融证券保险专业认证”2024年“君澜专业领航奖”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实习导师

卓信宝-机构配资开户-配资网大全-新手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